不论是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还是在对小说历史的巡礼以及对小说边界的询问中,米兰昆德拉都自觉地将对“小说家”这一身份的思考作为以上对小说进行勘探的基础,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小说家”身份,在其理论随笔中不断对“小说家”进行界定,并在其小说文本中开拓“小说家”驰骋的无限疆域。
“在昆德拉眼中,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与文学技巧,更是一种生存智慧和人生观念。”昆德拉将自己的思考与写作纳入欧洲小说传统之中,他既是继承者,他延续着自塞万提斯以来小说力图发现存在的不同方面、展示人庞大并富于生机的生活世界的传统。又是革新者,他对于革新的强烈诉求既出于他作为一位小说家拥有着十分独特的艺术个性以及使命感,也与他特殊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昆德拉将自己的复杂、漫长的人生缩略为 “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自1975年起,在法国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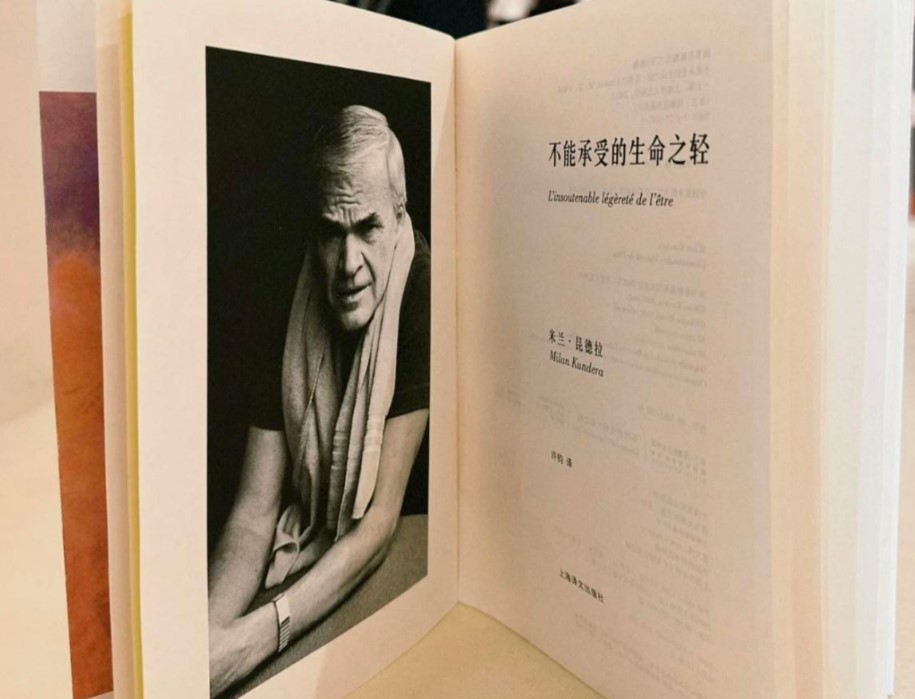
2019年将近结尾时,流亡法国43年、年已90岁的米兰昆德拉,重新获得了捷克国籍。我觉得,本身就是个很米兰昆德拉式的冷幽默故事:先前,他自己一直在各色访谈里说,自己只想当个普通小说家,而非一个流亡作家。的确:昆德拉是个流亡作家,按没有像一个典型的流亡作家那么(按照许多人想象他应该站的立场)来写作。
他对德国《时代》周刊说,自己没有返乡梦,因为“我把布拉格带走了:它的气息、味道、语言、风景和文化。”然而终于,他还是得回了这个国籍。在他的名作《生命不可承受之轻》里,萨宾娜从捷克去了西欧。她不喜欢身在布拉格时遭遇的重压,但也不完全赞同另一边对布拉格的刻奇看法。与如今“我只是个普通作家,我不是个流亡作家”的昆德拉,因为重获国籍而上新闻……看去有些相似吧?
没有等到米兰昆德拉捧得诺奖的消息,今天我们却收到了他离世的噩耗。中国台湾地区作家唐诺在写给昆德拉《庆祝无意义》的一篇书评中说,诺贝尔文学奖“不太敢要、甚至畏惧那些一下子超过太多走得太远的东西,那些太过复杂以至于无法顺利安装回当前人类世界的东西”,昆德拉的写作便属此类。

他问,昆德拉本人还在意诺贝尔吗?又以《庆祝无意义》本身的体量、题材和写法判断,不,他不在意。昆德拉自从1967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就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不仅把自己藏在文字之后,秘不示人,更无与伦比地试图将思想藏在小说之后——甚至,放弃纯粹的、哲学的、思想的表达。
《巴黎评论》的采访者问他,“为什么一个小说家会在他的小说中,想要剥夺自己公然地、独断地表达哲学观的权利?”昆德拉以一种几乎冒犯的方式揭穿了对文学的误读方式之一:“人们经常讨论契诃夫的哲学,或卡夫卡的,或穆齐尔的,但只是为了在他们的写作中找到一条连贯的哲学!他们在笔记中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发展成智力练习,玩似是而非,或即兴创作,并非一种哲学的断言。写小说的哲学家,不过是用小说的形式来阐明自己观点的伪小说家。”
这在昆德拉身上形成了一组对立。正如法语学者、译者黄荭在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采访中所言,昆德拉是如此清醒、敏锐、通透,连他的小说名都充满着寓意和对人生的感悟,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庆祝无意义》等。而恰恰是他,放弃了对哲学的依附,甚至拒绝哲理小说作者的称呼。
点击收藏本站,随时了解时事热点、娱乐咨询、游戏攻略等更多精彩文章。





































